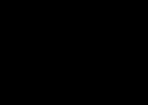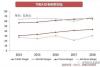华为基本法的源起
1995年,华为迎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年轻学者,彭剑锋、包政、吴春波等人。他们分别留学于美国和日本,回国后,翻译了大量美、日的管理学著作,并在国内进行推广,他们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学界的第一批“盗火者”。任正非聘请他们对华为的市场体系做一个组合的薪酬方案。在此之前,华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制度体系。
1996年初,任正非突发奇想,想请年轻的专家们为华为制定一部基本法,于是,另一个人登场了,他就是留学于美国的黄卫伟。从此,黄卫伟与华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彭剑锋等人结束与华为合作之后的将近20年,黄卫伟和吴春波一直在华为兼任管理顾问,近距离、长时间地观察和研究华为。
任正非对黄卫伟的评价是:“学术功底很深,现在还有几个人钻研大部头的西方原著?黄老师可是一本一本地在啃……”2014年5月,在黄卫伟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后的第三年,被华为聘为首席管理科学家。

《华为基本法》最初两页纸的框架由黄卫伟和包政构思,基本定位在回答三个问题:华为为什么成功?过去的成功能否使华为在未来获得更大成功?要获得更大的成功还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形成了战略、组织、人力资源和控制几大块,这是西方管理学的一般体系,但在当时的中国企业中却没有多少人能弄通并实行。

彭剑锋、黄卫伟、包政、杨杜、吴春波、孙健敏,即所谓“人大六君子”,他们将西方的“血液”融进了华为的东方基因中,这一步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20年前,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华为基本法奠定了华为文化和管理体系的基础
《华为基本法》最核心的部分是价值观:实现顾客的梦想。从根本上奠定了华为后来20年的价值趋向。华为早期走的是一条技术驱动的路线,到底是技术至上还是客户至上?在1996年前后,华为内部有激烈争论,《华为基本法》开宗明义将华为定位于“实现顾客梦想”,从而以“法”的形式使之尘埃落定。

时隔不到一年,在选择IBM还是其他美国公司对华为进行管理咨询时,为什么最终确定IBM?关键是IBM奉行“市场驱动”的理念,“这句话打动了老板”,孙亚芳回忆道。后来IBM在IPD变革中所推行的“端到端”(从客户到客户)的价值主张,不但重构了华为的研发体系,也重塑了华为的全部组织体系。
应该说,《华为基本法》与IBM在根本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在黄卫伟看来,《华为基本法》是对任正非管理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阐述。比如“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生生不息,华为没有可依赖的自然资源,就是在人的头脑里发掘大油田、大森林、大煤矿”,实际上定义了华为是经营人的企业。人是企业的最大财富,在这一概念下,从而确定华为是一个由货币资本和劳动资本(包含知识付出、企业家贡献)共同构成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体系;2009年确立的华为核心价值观中的“以奋斗者为本”的早期思想即来源于此。

任正非在《华为基本法》初稿中加入的另一段话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服务业,用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这既是任正非办企业的基本方针,又同时将华为逼上了“华山一条道”:充分聚焦与非多元化。这一段话在内部引起过很大争论,任正非力排众议:“一个字也不能改......”
《华为基本法》中关于“每年按销售额的10%投入研发,必要而且需要的时候还要加大投入”的观点,源自于华为已有的做法,但《华为基本法》将其固定了下来.
任正非在《华为基本法》第二稿中加进了“不让雷锋吃亏”“不迁就有功但落后的员工”等字句,让黄卫伟印象至深,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暗藏杀机”——这恰恰是许多创业企业走到一定阶段的大坎,华为以铁的律条将其化解了,这也标志着华为是按照现代企业的契约观而非人情观驱动发展的。
华为基本法曾八易其稿
《华为基本法》八易其稿,中间经历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上上下下的讨论与争论,既熔铸进了许多西方的管理精华,也充分提炼了华为10年发展的成功实践,集中了华为不少年轻管理者的思想火花,尤其贯穿进了创始人任正非的宏大理想、国家主义情结,以及建立在对人性深刻洞悉基础上的一整套管理思想。
客观而论,《华为基本法》于华为而言,真正起到的重要意义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创立不到10年的华为,高速发展的背后潜伏着重大危机:主义林立,思想多元,充满了活力,也充斥着混乱
“黑猫白猫”抓到了许多“老鼠”,但“各路诸侯”的自由发挥所带来的思想与组织层面的动荡也露出端倪,如不能从根本上进行厘定和约束,持续下去,将会酿成一系列问题。

《华为基本法》是华为历史上的第一次“顶层设计”,尽管参与起草的学者们大多是留美留日人士,但其内容、架构、叙述方式以及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仍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思想发动重于制度设计。某种意义上,它是华为为引进西方顾问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的思想前奏,是在为后者的登场“清理盐碱地”。
当然,《华为基本法》也不具有“法”的性质,它更像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纲领性文件,而不构成对全体股东、管理者以及员工的“强制性遵循”。比如《华为基本法》中讲的“事业部制”的组织模式,在华为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因此,《华为基本法》更多的是一个阶段对组织和个人的“思想软约束”,“法”的表述仅是借用而已。
华为后期一系列变革从未脱开基本法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