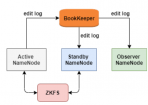“人工智能”对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普通人而言,早已不是一个畅想性的、高山仰止般的概念了。自从字节跳动和拼多多这类企业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自家产品中后,这个几年前还是很未来的概念更是开始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回溯这个概念走入大多数普通人的视野,还是2016年的AlphaGo战胜围棋选手李世石的新闻。4年不到的时间里,便逐渐让我们觉得习以为常,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发展不可谓不快。
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一直都这样顺遂。
关于人工智能最早的追溯,可以到上世纪50年代。1950年,图灵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算机器和智能》的论文,第一次正式提出机器智能的议题。
6年后,以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基和克劳德·香农为主要成员的达特茅斯会议召开,约翰·麦卡锡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此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也慢慢起步。
但是,最初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思路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相同。当时的人工智能追求规则和逻辑,被称为符号主义。而我们当下常见的人工智能则是基于模式识别的统计系统,被称为联结主义。
在“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提及之初,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所谓智能机器就是像人一样的机器。因此,机器要获得智能,就得向人类学习。解决智能问题的路径也成了先了解人是如何产生智能的,然后让计算机按照人的思路去做。因此,这条研究路径极为注重规则和逻辑推理。
遗憾的是,按照这种方式研究了十多年后,没有出来什么有用的成果。到上世纪70年代,一些人开始尝试用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去解决一些机器智能问题,诸如语音识别、翻译和图像识别等。
一开始,相比于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并没有显示出特别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潜在好处,就是随着数据量的积累,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好,识别准确度也会越来越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数据开始呈爆炸式增长,联结主义的路子也越走越宽,迎来了突飞猛进。而传统的符号主义则很难从数据量的提升上获益,至今也鲜有突破。
对于两类人工智能的区别,《人机平台》一书中用成人学习第二语言和婴儿学习母语的比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就里。
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时,会从语法入手,也就是从规则入手。想想我们学习英语的过程,首先要了解句子包含哪些成分,词性有多少种,什么词能做什么成分,什么时候用什么时态等等。规则不仅多,而且常常还会出现很多例外,让人难以把握,痛苦不堪。

而婴儿学习母语时则没有这种苦恼,在上学之前,他们从未接触过明确的规则指导,只是通过倾听父母和周围人的聊天,然后辨别其中的规则和模式。这其实就是用统计原理去辨别语言模式,先摄入大量的数据,然后从数据中提取共同点,形成正确的认知。
为什么成年人学好第二语言的比例甚少,而婴儿却都成功掌握了母语(除非身有残疾),这其中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联结主义突飞猛进,而符号主义进展缓慢。
尽管联结主义为主的人工智能在当下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也并不意味着符号主义被“判了死刑”。专业领域依旧认为两种方式各有优劣,解决的是不一样的问题,相关的争论也一直持续着。
两类人工智能在思维模式上的不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哲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即关于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在世界观上的不同。
与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一样,都希望从变化无常的事物中找出永恒不变的事物。
如果稍加留意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全天下的马都是一样的,尽管没有两匹完全相同的马,但是有些特质是所有马都具备的,这些特质使得我们可以从众多事物中认出马就是马。尽管一匹马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会变胖或变瘦,会瘸腿,会死亡。但是其所具备的马的“形式”是永恒不变的。

据此,柏拉图认为,有一个比感官世界层次更高的“理型世界”存在,所有感官世界中的事物,都是对理型世界的拙劣模仿,或是以理型世界的事物为模子,复刻出了感官世界的事物。
比如,感官世界中所有的马,都是理型世界中“理型马”的复刻品。感官世界中所有的马的特点的集合,是理型马特点的子集。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感官世界中的同一种事物的个体间会存在差异,因为只有模子是完美的,而复刻品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
在柏拉图看来,理型世界在先,是更高层次的,而感官世界在后,是低层次的。
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感官世界之外并不存在一个理型世界。我们之所以能够认出马是马,并不在于有一种理型马的存在,而是我们在见过足够多的马之后,无意中提取了这些马的共性,形成了马的“形式”,正是这一基于大数据的模式提取过程使得我们能在众多事物中认出马是马,而不是别的什么事物。
再来看看人工智能的两种研究思路。符号主义有点像柏拉图,把人视为人工智能的“完美理型”,人工智能是对人类的一种模仿。其实我们不难设想,按照这种思路,很难让人工智能真正超越人类。
而联结主义则有点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规则和逻辑也是事后总结的产物,而并不是先于人类出现的、支配人类行为的“理型”。因此,先不去管什么规则和逻辑,而是给机器提供大量的数据,让机器从数据中提取隐藏的结构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算力更为强大的计算机很容易发现人类都难以意识到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AlphaGo能够最终战败人类最厉害的围棋手的原因。

绝对的错与对是很难界定的,但是短期内产生的效果却不难衡量。在当前看来,联结主义在创造价值和推动变革上是优于符号主义的,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对今人而言比柏拉图的世界观更容易接受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这种隐约的关联中看到,尽管技术的更迭日新月异,相应的产品也在快速地推陈出新。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推动突破与变革的内核,依旧是人类如何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
尽管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人类,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依旧有人的用处。哪怕是在最前沿的创新和技术变革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可能依旧是能否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同样,一个蕴含着巨大潜力的新机遇得以突破的关键,往往与一个存续已久的老问题有关。